「文學」出現「典範」爭議其實並不意外,問題是討論「依據」。而且重點是,不同詮釋觀點應該在作品解讀「幫助」,而不是「阻止」。有時候「讀者有全面的詮釋自由,怎麼看怎麼是」會淪落一種相對主義,最後
文評就是「讀者」各持己見的各說各話,那關起門來寫作,不就好了,何必交流?而且,作者不也是一種「特殊的讀者」?他看自己作品,是否會與他人有所差異,這也是「詮釋學」關注的面向。
我其實不太熟詮釋學,儘管讀了一些理論和發展,但依稀感覺,那跟我以前學的「符號學」不是同一類型的學問。符號學可說是一組分類基準,將文本要素拆解丟入,可以產生有趣的分類,幫助「詮釋」。「詮釋學」不只是研究「讀者如何詮釋作者」,更研究這種「讀者寫出了讀書心得或註解」,後面的讀者怎麼研究這種「文本互涉」的結果。
譬如:孔子的弟子記載孔子言行,編《論語》,毋寧就是對「孔子」的文本進行詮釋的結果。後代漢儒又怎麼讀論語、且替其注疏;宋儒理學家又如何解決「孔子」、「孔子弟子對其的詮釋」、「漢儒對前兩者的詮釋」、「其他宋儒對前三者的詮釋」。
如果,用傳統的詮釋方法,就是訓詁。《論語》的意義,決定於注疏的內容,末,《論語
》的意義便一脈相承。孔子決定了《論語》的意義,接著,孔子的弟子只是讓孔子的意思更明顯,漢儒、宋明儒者(※尤其是朱熹的四書集註,是論語的權威辭典)亦是如此......但得問個問題,語言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有意義的遺失或轉換?而且孔子不會誤講了自己的思想?孔子的弟子就「編」對了孔子?漢儒、宋儒、明儒這樣一脈下來的註釋,都完整的呈現《論語\孔子》的意涵?
所以,羅蘭‧巴特提出「作者已死」的詮釋觀。但他的意思
並非「隨便讀者講」,而是「
不用擔心你講不對,不符合作者或古聖先賢的制訂,反正就說吧!共同排除偏見和傳統,一起討論。」
這也結合了「康德認識論」的主張:「人無法認識本質,只能認識現象。」既然如此,人何必交談和交流?反正大家認識的東西都不見得一樣,而且沒有一個人能認識現象內的自在之物。
「現象學」提供了解決方案:雖然大家都無法認識本質,但在面對現象時,大家都在腦內形成了「本質的仿造」,
彼此可以溝通這種「本質的仿造」。譬如你我都知道一個關於「曹操」的符號,但你認為曹操指涉「
奸雄\曹操A」,我認為曹操指涉「
英雄\曹操B」,如此,我們便可交換我們對「
曹操A\曹操B」的認識,使我們更認識「
曹操」。而
這過程,敞開心胸且連續的溝通,絕對必要。 最後,講個個人的實例感慨作為結尾。
我想到我曾經一度喜歡,現在卻放棄的高中學妹。在她所寫作的小說中,我們進行了交流。某次我們之間友人拿她的小說情節開玩笑,作出崩壞角色的「情節預寫」,基於知道作者\學妹開得起玩笑,我也跟進。
但當作者出來表達意見的時候,我卻因對其劇情鋪陳開了玩笑而心有愧疚,對她道歉。她的主張是「讀者有詮釋的自由,而作者也有自行寫作的自由」。雖然學妹展現了一種作者風範,但相信我們溝通的不是同一件事情。
我道歉,是基於「態度的不尊重」,刻意崩壞原本小說的背景、人物設定,扭曲了她的情節發展。如果我態度很認真,並認為如此情節發展是我設想的,那我不會道歉,而且會希望學妹\作者有雅量聆聽我的想法。儘管如此,學妹似乎認為,無論讀者尊重作品與否,仍有詮釋的自由,但
某方面來說,她便沒有思考「讀者詮釋作品,是否以尊重為前提」的價值問題。
這就讓我有種感想:
某些作者口中喊著形同「作者已死」,「讀者有自由解讀的"權力"(power)」,是不是某種自我保護機制?可能她們想留住讀者,所以由此建立讀者的信心\正當性,使讀者能繼續說話,且認為作者是個和藹和寬宏大量的人?那,這可能誤解巴特提出「作者已死」的更深一層的涵義---「促進文本意義的匯集及討論」。
儘管這麼說,我也是在談「兔子所認為的巴特\巴特A」而已。但溝通不就是這樣嗎?不然我這篇文章鎖起來,自我欣賞就好了。
※追記 剛好找個機會把這段認識寫出來。而且真正刺激我想寫的是我學妹(笑),那是後話。以下補充我的觀點:
一、並不覺得得作者需要負責,某方面,作者可以為自己寫作,那自己就是自己的讀者,寫給自己高興,任性得寫,又何妨?---「如果作者寫文,就是其自己閱讀所創作的。作者也是為讀者寫作,只不過那讀者也是作者自己本人而已。」
二、作者一定具備一定的自由權,甚至作個比喻「一個人不願意把話說清楚到讓人聽懂,他犯了甚麼罪或道德瑕疵嗎?」那我想,我們都不該跟小BABY說話,因為小BABY一定聽不懂,更重要的,我們無法驗證小BABY是否聽得懂(※有客觀的"聽懂"存在?還是只是行為主義研究下的定義?)。
三、上述兩點,我都很尊重,尤其我自己也是作者\讀者,甚至評論者。而若把意涵弄得更清楚,對「分析\詮釋」是有幫助的。當一個人指出「你面對的頻果這面,『可能因為光線問題』,可能看到的不只是頻果,甚至發現這頻果是保麗龍造的,而非天然的,這不是很有趣嗎?」如果不聽到這類意見,我想自己不見得能發現「這個物件\文本、還有這種可能」。我想,閱讀不是為了找出標準答案填考卷,而是娛樂\自我提生的過程。
最後,上昇到哲學層次討論,真的有所謂責任義務?我想不必然。作者對文本,甚至對讀者都沒甚麼義務,更應該說,就連作者都可以認為,自身對自身不具備任何義務,而在我所認識的倫理學,這也是存在的價值信仰,被人主張過。
※讀文,評文、寫文,就像交朋友一樣自由。儘管自由,卻沒辦法強迫別人喜不喜歡自己、願不願意\能不能理解自己,與自己交朋友。
※寫文,也沒辦法強迫他人看、看懂,用哪種方法看、甚至讓別人喜歡自己的文章。
※讀文、評文,可以自己看、判定自己有沒有看懂,用甚麼方式看是適宜的。與他人交流這些意見,但不代表有互相接受的義務。但我想,觀點不同是無所謂的,溝通重要的是禮貌和尊重。
這些都是自由的互動,但也因此,「不該強迫任何人」,是自由底限。 延伸閱讀
- 兔靖語編,&_伽達默爾與詮釋學:理解的循環_&
- (推薦閱讀)林維杰,詮釋學是什麼? (屏東教育大學演講綱要)
- 中文在線百科,詮釋學
- 高達美的詮釋學
- 畢恆達,詮釋學與質性研究#詮釋學與紮根理論,199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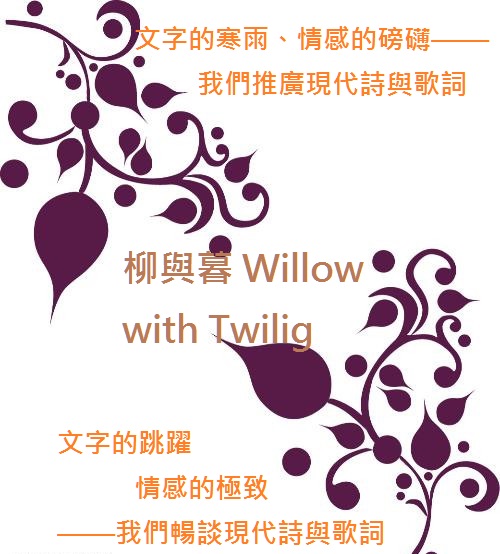 誠摯邀請您
誠摯邀請您